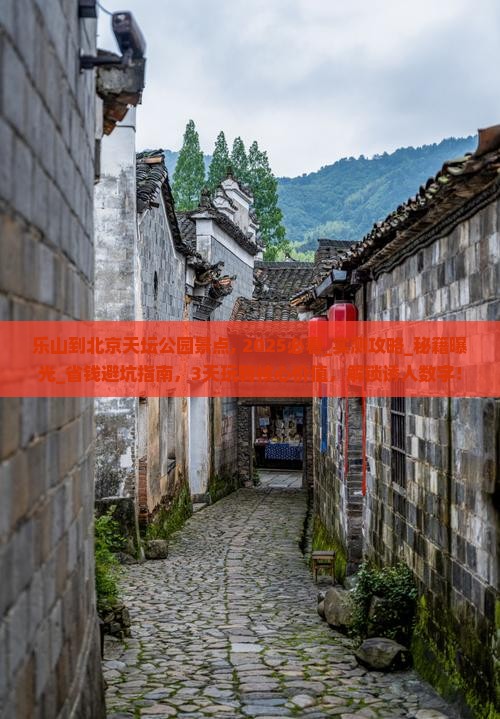Q:在去正面连接之前,已经准备好要写来自遥远国度的故事了吗?
A:不完全是,我决定回国做新闻,其实是因为觉得外媒笔下的中国永远特别宏观,采用宏大的叙事风格,从政府政策、政客或者经济方面来写,那不是我想做的中国报道。当时我认为国内的《人物》、正面连接、极昼工作室这种做特稿的平台是很有冲劲的,敢于去触碰社会议题,也让我看到很多平时看不到的社会问题。所以当时我选择去正面连接,其实更多想做国内的报道。但是后来我发现做国内的选题的时候,我并没有一直在国内读书工作的记者有经验,反而国外留学的经历、会说英语,可以跟更多说英语的采访对象沟通,成为了我的一个优势。
国际新闻其实也是我感兴趣的领域,中国没有太多的国际新闻,我的技能可以让我把一些国外的新闻带给国内的读者,这也是信息沟通的优势之一。所以我不是一开始就有打算要写国际选题,而是之后逐渐发现,这好像是最适合我写的。
Q:来自远方的故事是否会占用互联网的公共空间?这种类型的选题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有什么意义?会怎么看待那些认为“远方与我无关”的评论?
A:首先,我们所探讨的并非实体的互联网空间,而是虚拟的。此空间极为庞大,其中存在大量的互联网废料。我不认为撰写一篇关于刚果、海地或者苏丹的报道属于占用公共资源。新闻是一种信息贡献,我撰写一篇报道并将其纳入公众能够接触到的公共信息库中,这不属于占用公共信息,而是增加了公众可获取的信息。我并未撰写无聊的娱乐八卦新闻,我所写的人物也是有自己的需求的。并且我不认为只有与我使用相同语言、在同一国家成长的人的需求才是真实的。
我能理解这种评论背后的情绪。在报这些选题的时候,编辑也会提醒我,这不是国内读者最感兴趣的话题,因为大家自己已经过得水深火热了,可能没有那么多同理心再去分给很遥远的地方,这些我能理解。但是我觉得基本的共情依旧会存在,如果有一天,这种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当然也不会希望外国人都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放任不管。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尼日地亚女作家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埃写过,“我们死去的时候,世界沉默不语”。
从直觉上来说冷漠对待这个世界就是不对的,作为一个想从事新闻行业的人,既然我有能力去讲这个故事,那就应该去讲这个故事。至于读者,如果他们真的很不爱读,那他们可以不读。但是对于有兴趣去了解一点中国之外的事情的人,了解外国的故事对他整体的信息框架和知识框架的建构是有好处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孤立的中国。
所以我觉得如果只关注国内的新闻,就好像你只理解你生活的一小部分。所谓中国报道或中国故事也不止发生在中国,在非洲大陆上就有数以万计的中国移民劳工,欧美、东南亚等地方也都有非常多的中国劳工,他们的故事也是所谓中国报道中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布局等,这些也都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只不过因为发生在国境线外,好像不被纳入到我们平时的视线里。但我不觉得应该让国境线去定义你应该关心或不关心什么。而且中国在整个全球舞台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多去了解中国人、中国企业、中国政府在海外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应该做的。
Q:全球右转、民族主义思潮兴盛的当下,我和很多身边的朋友都会感到痛苦,觉得怎么去写作都无法改变现实,有的时候甚至无法写出来这种痛苦。你在进行这样的写作的时候,是痛苦的吗?
A:政治抑郁与写作,二者既相互分离,又彼此促进。我能够写作、从事新闻工作,具备这样的技能,这可以成为我对抗全球右转、逆全球化趋势的方式。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反抗潮流的一部分,这样想让我充满动力继续写作。
不过确实我时常会有疑惑,我写了之后,这东西有人看吗?即便有人看了,看完之后又会有什么其他影响和意义呢?嗯……我不知道,但很多时候我试图安慰自己的方式是,确实我好像无法看到手机屏幕背后的读者读了我这篇文章后有什么变化,但我自己也是被各种信息所影响成长起来的,比如《南方周末》兴盛的那个时代的记者的影响。既然我能被他们的文字所改变,那说明也有人会被我的文字改变,只是我看不到具体的场景或人物。我有时会通过这种逻辑给自己某种信念。
我能理解被时代抛下的无力感,但在无力的时候如果再不做点事,不就更虚无了吗?在美国,教授们有时也会讨论希望之类的话题,大家认为希望、恐惧或者无力,这些都是私人的情绪,对于想要改变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帮助。唯一实际的就是去做事,可能做了事不一定有直接成效,但要是一开始就不做,那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先有行动才能谈及改变,不能只是坐在家里,期待世界变好。
可能我更多的无奈是,我写的文字并没有被真正读懂或读到,这会让我有无奈和遗憾。但我也看到很多正面的评论,说很感谢我让他们看到国际新闻的另一面,有一两个这样的评论就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白做。
我在写的时候并不是抱着“我今天写这篇稿子,苏丹内战就会结束”的心态。虽然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完全健康的社会,但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各个领域的人相互合作,而不是把所有责任都放在一个职业上。我知道很多律师,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也非常沮丧,总是想着我用一个案子就能改变不健康、不合理的法律,记者也会想着我用一篇稿子就能结束刚果的某种现象,这些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本身也不只是一个人的责任,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合作才能实现。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会让每一部分的人都感觉到孤立,觉得所有责任都压在自己身上。其实本来不应该是那样,没有人会指望一个记者用一篇稿子改变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
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讲的,有时候写这种远方的故事,会感到一种很无力、很虚无的感觉,会问自己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我的采访对象告诉我,有意义。我觉得没有人比真正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更理解意义和希望。既然他们说有意义,我信任他们,选择他们作为采访对象,那我就要信任他们的希望和对意义的看法。
Q:如何建立起和采访对象的联系,并且获取他们的信任?
A:横向找学者,找一些 NGO 负责人。学者的话就是找相关国家的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如果是 NGO 的话,就在 Instagram 上面搜一下。如果能找到之前报道过这方面选题的外媒记者,也可以去问他们有没有可以介绍的采访对象。
Q:采访对象英语不太好的情况下,文字交流可能会存在误解或者不完整的情况吗?
A:我们生活在 ChatGPT 和 DeepSeek时代,完全可以跟对方说你可以用最舒服的语言跟我交流。然后你再用人工智能翻译成英语或中文就好了。我觉得在现在不是问题了,我现在还在学法语,但是我也直接用翻译软件,跟法语区的人短信交流过,也很顺畅,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Q:采访前会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工作吗?
A:先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的基本情况,比如 GDP、地理位置、官方语言和首都这类基本的常识,同时把过去以来国际媒体中已有的与选题相关报道都过一遍。
我平常信息摄取渠道比较杂,国内的公众号我会看,像纽约时报之类的我也会看,有的时候像纽约时报、路透社这种大的国际媒体,对国际新闻跟进很快。所以我很多时候就从那上面找选题。
Q:翻译或者转述非母语材料的时候,会在确保原意准确表达方面遇到挑战吗?
A:会,比如有很多很具体的东西可能很难翻译出来,或者一些笑话可能只是在某一种语言里好笑,换一种语言就不好笑了。这也不是新闻本身的问题,而是翻译两种语言、解释两种文化就肯定会有的挑战。只能尽我所能把它翻译得比较像人话。
Q:如何把比较遥远的故事处理成中国读者更容易理解的稿件呢?文化的差异会不会对写作产生影响?
A:其实都是人的故事,就像我们也会读国外的小说、看国外的电影,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也没有想要处理成中国观众能看明白的形式。人性是共通的,很多时候,只要我能把我写的这些人身上的人性写好,我觉得大家不会不与一个真正鲜活的角色产生共鸣。
我很少会从文化背景这些角度来思考,我更多还是更好奇这个个体他的过去、他现在的焦虑和希望、他对未来的看法。我更感兴趣个体的故事,而不是整体的文化。
Q:如何确保新闻客观?
A:我觉得就是要确保你写的选题里涉及到的各方人员,在英文里我们叫 right to response,给到相关方阐述立场的机会,尽量做到客观。
Q:听起来好像所谓的国际非虚构跟我们国内的非虚构写作中其实隔的不是很多,可能隔的只有语言。
A:我觉得没有那么大区别,其实本质都还是新闻。但你给美国读者写中国的新闻,还是会解释很多,提到清零和封控,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几个词后面代表的是什么,但你跟美国人单独讲我们有清零政策,他们就会问你清零政策是什么?如果是给不同文化、历史、社会背景的人写作,你需要展开叙述很多背景。
它肯定会影响整篇文章的美感,但是新闻还是信息增量更重要一点。
Q:会有一些推荐的书,或者说推荐的渠道去学习国际非虚构写作吗?如果对国际议题感兴趣,应该从哪里开始学习呢?
A:我最近读到的最喜欢的一本书叫《饥饿》,是个阿根廷作家写的,讨论为什么全球生产的粮食理论上足以养活 120 亿人,但事实上却有 10 亿人在忍受饥饿。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他应该是花了十几二十年去走访各个国家。韩国文学对我也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加勒比地区的后殖民写作。
关于写作国际新闻,首先要学好一门外语,不一定非要是英语,像法语、西语都可以,看你想具体写哪一个区域的人,这些都很有用。去关注你关注的地区,可能可以慢慢发现选题。
A:新闻其实还是不能指望在课堂上学,我觉得新闻是在实操中学到的,在课上老师可能会带我们看一些别的记者写的作品,但是我个人总是感觉会有一点抽象,讲的也都偏理论,会有比较多对于新闻伦理的讨论,但是我觉得其实看你具体在操作的选题是怎么样的。我对新闻的理解更多还是来源于实操。